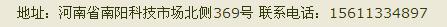小说鬼
《鬼》阅读须知你,对。就是你,朋友,来,靠近点儿,问你个问题——你怕鬼吗?我怕。我怕鬼,我怕鬼,我最怕鬼了。最怕了。我打小就是个胆小的人,像只老鼠一样。我怕高,我怕乌黑的人群,我怕巨大阴沉的人民礼堂。我怕禽类,我怕昆虫,癞蛤蟆会直接要了我的老命,蛇,噢蛇,女娲造蛇的时候估计也是提心吊胆的(你要说女娲本身就是条蛇,那就有些勇敢得不讲道理了,朋友),不得不说,不管造物主是土地老儿还是耶稣基督,指定是个胆大包天的人物。我还怕痛。连纹着身、打着耳洞的人都让我害怕,朋友啊,人究竟是为什么要自寻痛苦啊?医生阿姨,你不给我糖吃吗?那我就不打。你真的没听到吗,医生阿姨?口罩堵住了你的耳朵吗,亲爱的白大褂?你听到那针头里传来的哭声吗?那孩子漆黑的哭声。但以上诸种,哼哼。以上诸种,都没有鬼来得更让我害怕。我从来没有听完过一个鬼故事,实话告诉你朋友,我也从来没有看完过一部恐怖片。我试过各种方法,我试过,我发誓!比如默念核心价值观或者佛经之类的东西,像在身上罩上件隐身衣,去蒙混那些鬼怪出没的时刻,但并不作效,见鬼,啊我操,真是、见、鬼、啊啊啊,没用、没用!此外——此外,我得平复一下自己的情绪了,不让自个儿老是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咕咚咕咚地往肚子里灌凉白开。此外,我还能从任何一首曲子里听出瘆人的弦外之音——听我说,我是说任何曲子,哪怕是《我的祖国》。除此之外,我还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朋友,嘘:鬼,鬼是在夜里出没的。哼哼,嘻嘻嘻嘻。因此,理所当然,我害怕夜晚。白天才是我的房子,绝对的。天黑之后,我哪敢独自上楼?恐怖的房子。房子是要死不得的酷刑。要是让我摸黑上楼,上到几楼我就会从几楼跳下来,在那之前我还得克服恐高,活着就是这么件勇敢的事,不是吗?即使有盏灯点着,我也要做足漫长的——“心理建设”、“抑郁辅导”、“催眠疗法”,医生阿姨,你是这么说的,对吧、对吗?嘻嘻。回答正确,我从来不找有电梯的房子(也就是太高的房子)。从不。夜里,我不敢凝视——噢,我哪敢用这样的词?——哪怕是瞟一眼窗户或者任何具有镜子功能的东西,我都不敢。我不敢在午夜时分睁着眼睛,不敢在四下无人的房间回头,谁都别想叫我在夜里出门。我从不在夜晚写作——哎呀哎呀,你看我,都忘记自我介绍了,本人是个业余作家(话说回来,像我这样的人,不写点什么就真的没个塑料罐罐值钱了,你说是吗?我是说像我这样絮絮叨叨、神经兮兮、过于敏感又说个不停的人)显然,这些文字是在一个明媚的白天敲下的,并且我向您保证,一字一句写下这些恐惧时,我脑后早已经有成片的鸡皮疙瘩蹭蹭地往上冒,像一层一层地在蜕壳,是的像一条S——我就不说出那个字了。即使是白天,我也害怕正有一个鬼躲在我身后的衣柜里,不,不不,我开始不由自主地发抖了!此时此刻,我怕键盘突然失灵,我怕屏幕上出现异常的像素。见鬼、见鬼!你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吗?一只小虫突然飞过,不信你看我满手的汗。确实,我必须得忏悔,我是一个失败的唯物主义者。但一个胆小鬼能做什么呢?只能仰仗伟大的科学和伟大的马克思。科学告诉我,人类大脑的某个居委会(叫杏仁体什么的)管辖着“恐惧”,说白了,感到害怕不过是这个杏仁突然受了刺激,外国就有这么个人脑子有问题——杏仁坏了、真坏了、坏得透透的、坏得死死的,他就从来不会感到害怕,看恐怖片就像喝凉水,哪怕有歹徒把刀架在他脖子上(这是真事儿),他还能冷静观察那刀够不够锋利,能不能剁碎骨头。朋友,我真是羡慕这洋人。坦白讲,说这些我一点不觉得害臊,因为作家的品质之一就是高纯度、不掺假的真诚,纳博科夫的话(所谓作家是骗人的魔术师)我是不信的。我嗤之以鼻。研究蝴蝶的人不可理喻。但读者朋友,接下来,呜……接下来这些话,就可能会让我们之间这稍纵即逝的关系显得尴尬,变得靠不住脚,因为我要做一件对我来说堪比造物主的、胆-大-包-天的事。如果您还没有失去耐心的话,就听完这多少有点荒诞的起因再离开吧:是我亲爱的编辑女士G(我从没有见过她)向我约稿写一篇“中式邪典小说”(我想那女人大概是想尽早把我开了,所以才故意刁难我),迫于生计考虑(如果不写我是没法活下去了,我有家庭,一个大大大大家庭要养不是嘛),但同时更是因为,前一阵子——我、我一个最怕鬼的人——扎扎实实地见鬼了!为了贯彻我纪实写作的原则,为了生活——生——活,我答应了这个无理的要求。在此之前,我还特地鼓起勇气研究了大作家书写“恐惧”的经典文本,我为了写作牺牲太多了不是嘛,我一口气读完了爱伦·坡先生的《厄舍府的倒塌》、《泄密的心》、《黑猫》等等等(但由于害怕,我选择了英文原著囫囵吞下;哦吼,如果您还没有读过现在就去读读吧,一个人的时间毕竟是有限的,人的一生很短,相信我,花在文字上的时间尤其如是),经过了战战兢兢的回忆和举步维艰的构思,我最终决定把我的亲身经历写下来,是的,您的“期待视野”起作用了呢,您即将读到一个恐怖小说。但还是丑话说在前头,让我们打个比方(您知道,作家最爱打比方),假如这个小说是一个房子(或者说,一个鬼屋),房子的地基(结构)、家具(场景)、主人(人物)以及它的最终倒塌与否(情节)都会是陈词滥调的、缺乏悬念的(因为我太害怕了、这甚至干扰到了我的记忆和语言);但如果您真的看到了鬼,请您相信,不论“它”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它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它都是真的、死死的真的,这小说里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都是真实的——因为我真的看到鬼,我以我的胆小如鼠发誓,我发誓,我真的看到了鬼。当然,为了您的阅读体验,我也发誓尽力克服自己的恐惧而不让如上的碎碎念出现在这个小说里(您得知道这有多费香烟),小说中的“我”尽量会是一个话语正常、逻辑清晰、行为合理的、不那么神经质的——当然最重要的,不那么胆小的(众所周知,一个胆小鬼是没办法讲鬼故事的)——叙事者,如果我实在控制不住,那只能请您看在我的怯懦的份上,大人有大量啦。成了,很快你就会看到,这篇小说的题目叫作《鬼》。事情还得从一个月前的那个晚上说起。(编者注:黑体部分为作者万户特意标明。)《鬼》(上)直到夜很深了我都没能入睡,原因是楼上总是传来噪音。起先是脚步声,从远及近,有时伴随着卫生间的水流声,有时是那种尤其具有辨识度的、上世纪的带把手儿的陶瓷杯子与玻璃碰撞的声音。妻子侧躺着,用手枕着头,这阵子她正在备孕,我希望此刻她如潮的鼾声里最好还有另一个生命的声音。实际上,怀孕的问题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的正常生活,居委会的人上门拜访了我们不止一次,每一次我们都推推搡搡地像在菜场砍价,可人总是要吃饭的:我们必须得尽早生下第三个孩子了,居委会的语气越来越恶劣。但我们不再年轻了,受孕不再像做爱那么容易;久而久之,妻子的精神开始变得有些恍惚,总会说些模糊的话,我有时觉得这个枕边人就是那位意识流女作家伍尔芙提到的布朗太太,除了晓得她的左胸比右胸大一些,我发现自己对她所知甚少。在这个失眠的笼子里,沉睡的妻子就像我虚构出来的一个人物。这当然纯属扯淡。如果妻子是我幻想的,那么此时此刻我一定会让这个纸片角色醒着,陪我聊天解闷,陪我度过长夜漫漫。事实是,她正在梦里陪孩子呢。从五楼传下来的噪音再次把我拉回了这个该死的夜晚。这次,声音更加琐碎,也更加细腻了,这是我越来越敏感的神经在起着作用:男人的咳嗽声,随后是另一个人拍打他脊背的沉闷声音,如果我的耳朵没出问题,我甚至听到了水咕嘟咕嘟吞服药品的声音;哦不,他们居然开始刷起了短视频,循环播放着那个或许是这个国家最令人抓狂的女人的笑声,就是你想到的那个“魔性”笑声,好像有一只得了癫痫的黑猫住在她狭窄的喉咙缝里;大概循环了十几次,黑猫终于死了,接着又是一阵匆忙的脚步声,“兹拉——”,衣柜开了,我似乎听到了丝绸摩挲的声音,伴随着女人拨人心弦的微弱喘息。如果后来我再回想起这个夜晚,大概会同意一切都是从这“兹拉——”一声开始走向不可控的。说来怪难为情的,五楼的住户竟然开始行房事了,在这没个活人醒着的午夜时分。亲吻,嘴唇像鱼一样一开一合,一个个小气泡浮到鱼缸上;女人的呻吟,每个女人都有不同的呻吟,有的像风声,有的像乐器,楼上的女人则像是动物,具体来说,时而像雌雄同体的小兽,时而确实像发情的母兽。床开始有节奏地吱嘎作响,像一艘在浪潮里飘摇的船,啪、啪、啪,啪啪啪的声音不绝于耳,像白帆不断拍打着桅杆。很快,随着一声触礁的哀嚎,归于风平浪静。当然,像是经历了听力训练的我还是在源源不断地接收着二人筋疲力尽的呼吸声,男人“啪嗒”点起一根烟,烟草燃烧的呲呲声。此时,被噪音折磨的我已经疲惫得就像是楼上的那位男主人翁,但奇怪的事还是不由分说地发生。五楼的住户结束了短暂的房事之后,女人居然毫无征兆地开始了哭喊。那是截然站在“魔性”笑声反面的哭喊,但她也显然不是天使,我说过了,她做爱时发出动物的呻吟。可她是那么痛苦,撕心裂肺的,她在经历非人的疼痛;我想起开山的爆破,就像有万千碎石在女人体内炸开一样的疼痛,床单被她抓出了千百条沟壑,无法控制的双腿像落石一样砸在那张床上。而她的丈夫跟个没事人一样,再次开始循环播放短视频里魔性的笑声。在这交响乐之下,我的妻子竟然还是没有因此醒来,我想她一定是怀上了。所幸的是,痛苦的哭喊并没有持续太久,随着一声长叹,女人似乎彻底解脱掉了,魔性的笑声也就此打住。但怪事还在继续。哭喊结束后,紧接着,更加令人揪心的声音出现了——一个婴儿的哭声。不会有错,那稚嫩、脆弱但充满希望的哭声,只可能属于婴儿,为人父母的再清楚不过了,那也是我们夫妇梦寐以求的、想再次听到的新声。但是希望从来就没有书上所谓的那种解放意义,对一个失眠者尤其如此;即使楼上继续传来了幸福的笑声、父母逗弄孩子的嘤嘤声、儿童玩具清脆的叮咚声,我的痛苦仍旧没有减轻半分。直到这时我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撞鬼了哩。因为荒诞的事要是都聚在一起,人们也就见怪不怪了:很快,孩子稚嫩的脚丫落地,开始跌跌撞撞地跑了起来。地板是木质的。跑累了,他开始翻起书页,哗啦哗啦,一边背着“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一边流利地撕碎。他的父母也没有闲着,五楼继续传来麻将牌的声音,碰、吃、胡,但都是出自同一个女人,她运气相当好;还有酒瓶的声音,一连串沉闷的饱嗝,像大厦崩塌下来,而一个城镇蒙在鼓里,经历过工业时代的人会熟悉这种声音。接着是剧烈的摔门声,剧烈到像是门框做小了几码,把灰尘震得粉碎。一个变声期的少年大喊:“你们为什么要生下我!”到此为止,终于,我的理性——我伟大的理性——总算提醒了我:如果我没有做梦,那就是我撞鬼了;可皮囊还在身上,还疼,还痛还苦。我确定,我是实打实地撞鬼了。但真若到此为止,我大可吞服几粒安眠药、或者把头闷进被子、乃至叫醒我的妻子,把那些牛鬼蛇神驱逐出我的房子和我的脑子。但是今晚,菩萨们没有眷顾我。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不,是跑步声、笃笃笃笃笃笃、笃笃笃笃笃笃。再准确点说,是逃命。但怎么也逃不出五楼的房子。呼救。女人的呼救、少年的呼救、整个房子都在呼救。撕心裂肺的呼救。“救命!救命啊!……救救我们!谁来救救我们!”瓶罐破碎,桌脚、椅脚的指甲和地板摩擦着,翻起盖来,渗出血来。随着房子的呼救到达了顶点,“砰”的一声!一块肉重重地摔在了木地板上,似乎还保有弹性和温度。“为什么生你?为什么生你?为什么生你……”男人嘴里念叨着这段咒语,钝器敲击骨头的声音和少年、女人的惨叫有节奏地相互应和,一强一弱、一轻一重,而我那该死的耳朵——这该死的听觉还在告诉我,哪块是颅骨、哪块是胫骨、哪块是肋骨、哪里是颈椎、胸腔、哪里是肉、哪里是血、这是什么器官、什么内脏……“生你……狗日的,为什么生你……为什么……为什么生你……”虽然我还在一个劲地劝自己“这是鬼、这是撞鬼了、这不是真的”,像用胶布把自己整个缠起来,但我确实已经被吓破了胆。即便是脑子里杏仁体损坏的人,也指定会给这声音吓得肝胆俱裂。我承认,这一切发生得太快,我已经完全麻木,只剩下副躯壳在做着应激反应;我紧紧揪着被子,尽力克制着颤抖,只露嘴和鼻子呼吸以免自己窒息过去。我想象着还原案发现场的惨状,仿佛自己就是唯一的证人。这时,一滴液体落到了我的脸上,我伸手去摸,有些粘稠,我下意识地一闻,一股腥味。血。是血。事已至此,我又怎么控制得住自己?恐惧占领了我的全身,尖叫灌满了我的房子,但也就是在这时,楼上的住户竟然安静了。噪音静止了,只有滴答、滴答的血滴声,像是时间在流逝;“啪嗒——”,他又点起一根烟。地狱已然降临在这里,我的妻子还是没有醒来,真是让我有些哭笑不得。我虚弱地推着妻子,轻轻唤着她的名字。但是她依旧熟睡,仿佛这一切都只是我的幻觉;可我确实也不想她受到惊吓,这种恐怖的经历对备孕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但我再也没法呆在床上了,我得去看看我的孩子们有没有受到惊吓;事已至此,我能做的就是让我的孩子、我的家人远离楼上那个疯子、那个鬼。我轻轻推开了孩子们的房间,他们也在梦乡中熟睡,书架、小桌、婴儿床、儿童爬梯,静谧如初。真是爱瞌睡的一家子,我捏了一把汗。但此刻你若在我的处境,就不会觉得含情脉脉了。我必须思考对策,哪怕恐惧在一点点吞噬我的理性。我是一个男人、一家之主、我是一个公民、我是一个人,我有良知,我楼上的疯子杀人了,我得报警,是的,我必须得报警,这关乎生死,这不是那么随随便便的事情。正当我在客厅惊魂未定时,外边传来了一阵不紧不慢的敲门声。《鬼》作者注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写得还行吧、还行吧?我还是有一定天赋的,哈?有没有读着也觉得背后凉飕飕的,嗯?我再重复一次,本人所写都是真实的!你明白了吗,这才是这些个文字最最最最恐怖的地方!读者朋友,你是不是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五楼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别急,小说就要到高潮了,别急。(编者注:此节为作者万户原手稿中突然插入的部分,与正文内容无关。)《鬼》(下)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鸡皮疙瘩已经布满了我的全身,甚至已经蔓延到了整个房子的角角落落;一瞬间,我的大脑里闪现了十几个恐怖的段落,入室行凶、小鬼附身、红衣女人……我能感到心脏就要蹦出嗓子眼,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把它安抚了下去:“,我们是居委会的。麻烦开一下门。”我蹑手蹑脚走去,猫眼里果然是居委会的人,他们仨侧身向门,像极了三个瓷质的大头娃娃。“有什么事吗?”“三楼住户举报,说是你的房子里有奇怪的声音,吵得楼下睡不着。”——“准确的说,是恐怖、恐怖的声音。”——“他们说闹鬼了。他们说出人命了!”——“嘘!说话当心点!”——“呃,那个,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呃,您是不是在看恐怖片?”——“您最好把门开一下,让我们进去检查一下。”三个大头瓷娃娃像同一台机器的三个零件,共用着同一个发烫的CPU。事到如今,我也不再有多余的感情和理智做任何反驳,只是为了澄清保身,我赶紧打开了门向他们说明情况。“嘘……”我压低了声音,指了指楼上,“是……我怀疑,的男主人把他的儿子老婆都杀了……”瓷娃娃们纷纷瞪大了双眼,一边还在疑神疑鬼地往我的房子里打量。“不信你们听。”大家都安静下来,五楼还在不停地传来“滴答——滴答——”声。当然,我还能听到那个凶手在抽烟燃烧烟草的声音,大头瓷娃娃们估计就不行了。“人已经死了。那是在滴血。”瓷娃娃们都警觉了起来,他们面面相觑,细细簌簌地在说着暗语,然后,他们转向我,机械地鞠了一躬:“谢谢配合。但先生,鉴于您家里只有两个小孩,也还是请您跟我们一起上来一趟。”和瓷人打交道就是这样。他们的表面光滑,容易让人忽略了他们是被烈火烧出来的泥土的事实。他们着实易碎,仿佛不是血肉做的。无奈之下,我只好关了灯,和他们往五楼走去。我从来没有上过五楼。过道的灯是感热的,瓷娃娃们摸了好久才亮起来,伴随着霉臭的灰尘,像费劲打开一个尘封多年、结满蛛网的盒子。灯一开,我们中间忽然出现了一个一动不动的小矮人!瓷娃娃们被吓出了声来。定神一看,才发现这是个半人高、神情卑微的求子观音像,怪瘆人的,她的身上刻着些歪歪扭扭的字,已经无法辨认了。瓷娃娃骂了句娘,抬头寻找的门牌。五楼住户的平台要比四楼宽敞,户与户之间用铁栅栏隔着,有种难言的压抑。咚——咚……兹拉——门没有关。这个房间笼罩着墓室一般阴惨的氛围,只有深处一盏昏黄的灯点着,灯的四周弥漫着烟雾,光线扭曲在一起,像好多个死结;另一处幽暗的光源是台老式电视机,比起这个年代常见的液晶电视,它像是脑后多出了一个肿瘤,电视的声音微弱,鬼知道在放着些什么。光线似乎都躲开了这个房子,把它变成了一张泛黄的黑白相片。于是我们向着光源,走到黑暗里去。铺面而来的是一股生姜的刺鼻气味,整个房间像是被浸在用来去腥的腌味料里,仔细闻,还有葱、蒜、辣椒、八角之类的味道,任何接触过烹饪的人都再熟悉不过了,似乎只要把这间房子下入油锅,就会传来一阵令人食欲大增的香气。但与其说这是房子,不如说这是个洞窟更加合适一些。在昏暗的光源下,隐约能看出整个房子的构造——出奇地简单,没有隔间,进门就是一个巨大空间,四壁光溜溜的,但已经爬满裂缝,像从人体流下来的血。房子里没有窗户,地上随处都是塑料的空瓶破罐,几支废针管躺在地上,甚至有一支歪斜地插在木地板上。有蟑螂或者老鼠在游走,像在推着几块跌落的石头,虫蝇乱飞,让人全身发麻。家具就像是给之前的主人遗弃的,凌乱不堪: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张床、一个紧闭的衣柜、一台电视机、一个突兀的马桶,所有的家具都给裹着一层厚厚的看不清什么颜色的布,仿佛是在进行什么仪式。越往深处走,异味就越复杂,香烟味、药水味、食物的馊味、排泄物的臭味、甚至还有精液的骚味,木质地板踩起来松松垮垮,甚至有几处坑洼,苔藓和不需要名字的植物正在潮湿和阴影里长出来,这儿简直是一个下水管道。但是——我找不见死者——那被钝器锤烂到血肉模糊的死者。只有灯照着两个瘫坐的背影,一男一女,像两只受伤的禽鸟。我们一步步靠近,女人把身子转了过来。这是个中年女人——或者说女鬼。头发散乱,穿着一件丝质的睡衣,露出的皮肤不多,但结痂的结痂,小臂布满密密麻麻的针孔;最触目惊心的是她的脸,如果那称得上是一张脸的话:她的脸就像一张麻将的五筒。两只眼睛深深的凹陷进去,透不出来半点光;那只突起的猪鼻子或许可以作为唯一她生而为人的标志;颧骨与下颚之间形成一个凹陷,她的牙齿掉光了,嘴唇整个卷进了口中,萎缩得像一个肛门。“我们已经尽力了。”她说起话来,哀求的口吻仿佛一个跟死神讨要阳寿的老太太;含糊的话语,又像在嘴里艰难地咀嚼着一块骨头。“不……”瓷娃娃们显然有些害怕了,发出咯咯咯咯的刚孵出小鸡的声音。“求求你们了,我们已经尽力了。”我这才注意到女人的手里拿着一个洋娃娃,玻璃眼珠锃亮,玫瑰色的假发在灯光下有些暗沉,但还是一丝不苟,“宝宝今天早上还好好的。”男人依然背对着我们,凶猛地抽着他的烟,他瘦骨嶙峋,脊骨随着呼吸波动,像被过度开发的矿山;他身上的白色背心千疮百孔;即使点着了烟,手里还在捣鼓着火机,“啪嗒——啪嗒”地响。而我的目光停留在他身前的那张桌子,桌子被淡蓝色的布包裹着,那些布竟然是一只只严实平铺的口罩,另有几只胡乱地洒在地上,上面沾满了秽物。“我们每天都看电视节目。”女人继续说着,瓷娃娃们也望向了那台老式电视机,四方的屏幕里困着一个面色健康红润的孕妇,信号电波并不稳定,女人的脸不时地扭曲变形,但仍然保持诡异的笑容;配合着抽象得有些喜感的动画,她正讲解备孕知识。“不,不是,你听我们说……”可瓷娃娃怎么也劝阻不住这个女人,她好像已经失去了听觉,只是在不停地捂着肚子,一点一点垂到地上,她的拖鞋好像已经长出了爪子,抠着木质的地板发出刺耳的声音:“求求你们,我们今天已经做了三次……”瓷娃娃们似乎表现出了一丝同情,但瞥见男人迷雾里的背影,忽然又严肃起来,其中一个上前把男人的烟掐进了烟灰缸。烟灰缸里插满了烟头,看上去像一窝丛生的蠕虫。“你一天抽这么多烟,怎么可能生得出小孩?”男人转过身来,他的眼神涣散,嘴巴颤颤巍巍的,欲言又止。“求求你们,是我的问题,是我生不出来,不是我丈夫的问题,他很累了,很累很累了,要不然,你们弄我试试看。”“不,不,不是的。”瓷娃娃摆手说着,但女人还在哀求,无论如何都没法打断她。“停一停!疯婆娘!停一停!今天我们来不是为了这个,是楼下有住户举报,说听见了诡异的声音。”“三楼住户举报,说是你的房子里有奇怪的声音,吵得楼下睡不着。”——“准确的说,是恐怖、恐怖的声音。”——“他们说闹鬼了。他们说出人命了!”——“嘘!说话当心点!”——“呃,那个,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呃,您是不是在看恐怖片?”这时候,电视里的备孕节目戛然而止了,插播进来一段广告:广角镜头呈现出一个坐落于山林的巨大寺庙,接着从远到近,以此胪述着寺庙的细节:从大小佛殿、藏经阁、佛塔乃至和尚的住处。诡异的是,广告结尾,电视里的报幕员念出了一段房地产广告——时代钜献,城市之巅。这时我才发现瓷娃娃们光着脑袋,头顶戒疤像老式电话上的数字按键,而他们竟然都穿着和尚的袈裟。女人也终于停下了哀求。她面向三位瓷娃娃,眼睛从两个洞穴中探了出来。“你们、说的——是,鬼、吗?……”她一字一句地说。哀告读者亲爱的读者,我是《黑铁》杂志主编G。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告知您,《黑铁》撰稿人万户已于年7月14日凌晨安详地离开了人世。万户生前为我们带来了许多精彩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他的小说秉持客观再现、忠实还原的写作原则,常以辛辣的批判讽刺和深刻的现实关怀受到读者朋友的喜爱。《黑铁》杂志的8月刊将会刊登万户先生的遗作——同时也是他的恐怖小说处女作:《鬼》。据编辑部对《鬼》手稿的整理,《鬼》讲述的是一个万户亲身经历的超自然故事。在这篇小说中,万户以惊悚刺激又怪诞陆离的第一人称视角带我们亲历了一次“怪房客”式的恐怖冒险,以其颇具中式邪典气息的笔触夸张地勾勒了一出三孩政策下“人变成鬼”的畸形秀,辛辣的讽刺艺术又见蒲松龄之遗风,读来使人直冒冷汗,同时又揭露出深入骨髓的严峻社会问题。但是,该小说结尾未竟,万户便撒手人寰,给我们留下了永远的遗憾。斯人已逝,悼念的最好方法或许就是将万户先生的写作精神永久地传承下去。因此,《黑铁》杂志特别发布征文活动:为万户遗作《鬼》之未竟结局补阙,活动持续一月,后续我们将选出最符合万户的写作气质与文学精神的结局,刊登于《黑铁》杂志9月刊。敬请期待。默哀半分钟。万户遗作《鬼》结局补阙(读者C来稿)“你们、说的——是,鬼、吗?……”她一字一句地说。三个瓷娃娃僵直在原地,一言不发。女人伸出手指,往上指着:“六楼……六楼,”她竟然狞笑了起来,“鬼就在六楼。嘘……你们听……”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是的,六楼传来了“滴答——滴答——”的声音。访谈:L夫人&读者C(鼓掌)G:您好,C先生。编辑部看到您的结局,甚至有种是万户亲笔的错觉。他也常常喜欢用这种简短精悍的文字表现结局,或者是完全颠覆的,或者是开放式的,而您这个结局恰好是兼备二者。能谈谈当时是怎么构思的吗?C:您过奖了。我始终相信,万户一定留着一个更加完美的结局。其实,万户在这篇小说里隐晦地致敬了他的文学偶像卡夫卡,不知编辑老师有没有发现。G:我倒是想起了卡夫卡那篇《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鬼》里面无处不在的声音系统确实也是对塞壬神话的一种反写。C:没错。从内核来看,这也完全是一个卡夫卡式的故事,“目的虽有,道路却无”,包括小说里的人物,还有读者,都想找到“鬼”的真相,但等待他们的却是无尽的延宕和错位:四楼以为五楼闹鬼,而等到居委会的人来时(这里可以另外提一嘴,万户不怀好意地把他们比作“瓷娃娃”,显然是动用了china瓷器这个意思),万户(也就是小说中的“我”)却发现自己才是被三楼的住户误认为的那个“鬼”,而真正进入了五楼的房子(注意反复出现的“房子”意象,而非“房间”,我个人认为这里是有深意的),瓷娃娃反而更像是那对可怜的夫妇眼中的“鬼”,而真正的鬼却始终没有出现。G:所以您把真正的鬼继续引向了六楼?C:是的,当然,这是一种虚指,就好像卡夫卡《城堡》中那个永远都不会露面的城堡主人。在万户的小说里,这种虚无荒诞感有着更加坚实的现实基础,那就是在高压政策之下,互相构陷、互相举报、不断在永劫循环(注意小说里的佛教元素)里变成鬼又变成人的现代公民的处境。“鬼”又何尝不是每个现代人的幽灵般的政治身份呢?而《鬼》最终的未完成,似乎也昭示着它与卡夫卡那些未完成的作品同样的伟大气质。(鼓掌)G:说的真是太好了!我想,万户在天有灵,会为有这样的读者感到骄傲。而作为万户的遗孀,同时也是作家生前的精神挚友、灵魂伴侣,L夫人对此也一定有很多话想要说,那我们来听听L女士的看法吧。欢迎L夫人。(鼓掌)L:我们小区没有六楼。G:哈哈哈哈哈,L夫人真是幽默。C:哈哈,毕竟是作家的妻子,总是语出惊人。L:你们是不是根本没有读过他这篇小说开头的读者须知?C&G:……L:没有,对吧。C:呃,那段确实有点冗长,我读得可能不是特别仔细,时间久了就有些遗忘了。但是万户先生写得还是很幽默的,把那种胆小者特有的神经质和敏感脆弱写活了。L:没有读过,对吧。他说了,他写的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他从来不说谎、他根本不会说谎。但他真的见鬼了。我们真的见鬼了。我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我们真的见鬼了。我求求你们了,他太累了……所以,嘻嘻,呵呵,你们没有读过,咯咯咯咯,对吧。谁会真的在意一个靠捡垃圾为生、又没有生殖能力的废人写的东西呢?说到底,现在还有谁会相信小说里写的东西呢?C:L夫人,您得知道,小说是虚构的。就算是万户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小说也是有很多的虚构成分的……!L:我们小区没有六楼。他害怕太高的房子。因为太高的房子会装电梯。他从来不坐电梯的。我们小区没有六楼。G:嗯……L夫人,对于万户的突然离世,我们也都很难接受……但是……C:我天,就因为没有六楼就不能写吗?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作家了……G(轻声):嘘,别说了!C:在万户的小说里,你根本就是熟睡了一个晚上,你根本就没有醒过,现在你又口口声声说你自己也见鬼了,所以你丈夫和你之间只有一个人说了实话,对吧?再比如他说他是个“胆小鬼”,不敢在黑暗里干任何事——任何事!但他不还是跟着那三个居委会的上五楼了……你说万户先生不能生孩子?不不不,他在小说里可是有两个小孩,正准备生第三个呢(只是第三个有点困难而已,嗨这是你们夫妻自己的事儿)!提醒一下您L夫人,生不出孩子的在你们楼上,当然那可能也是个虚构人物,正说反说,不管怎么说,《鬼》肯定是有虚构成分的。嗨,真是抱歉,无意冒犯,您实在是太敏感了,您钻牛角尖了,L夫人!G:别……别介意,L夫人,他这人说话就是……喂,你差不多得了!L夫人可能就是太悲伤,把小说和现实里的一些事情搞混淆了。L:好的。好的。但我知道,他已经尽力了。无论如何,我们都已经尽力了。他只是太累了,抽这么多烟,太累了。那个电视机、那个房子让他精神崩溃了。太多鬼了。我们见到太多鬼了。不是你们让他写的吗?嗯?不是你们让他写的吗?但是不怪你们。就算你们不让他写,他也还是会写的。因为他真的见鬼了。他见鬼了。我们见到鬼了。他什么都得写下来。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就算是鬼他也得写下来。G:导播,够了,掐掉!C:这女人疯了。L:是啊。是啊。可是,可是啊可是,他这么一个胆小的人,这么一个怕鬼的人,怎么敢在小说中自己去见鬼呢?他已经尽力了。他只是太累了。太多鬼了。我们见到太多鬼了。这个小说里每个字、每句话、每个标点都是实话,如果你们还是不信的话,那就去吧,去我们的房子吧,去见见鬼吧,鬼还在那里,你们亲自去看看吧,鬼,鬼,鬼就住在我们的房子里,去见见鬼吧。G:导播!到此为止了!L:去见见鬼吧,去见见鬼吧,在我们的房子里,在我们的房子里。为什么你们还是搞不明白?求求你们了,你们为什么还是搞不明白啊?我们,我们已经尽力了,我们自始至终都住在五楼的房子里啊!我们今早就已经做过三次了,在五楼的房子里,宝宝早上还好好的。去见见鬼吧。你,对。就是你,朋友,来,靠近点儿,问你个问题——你怕鬼吗?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上一篇文章: 李居明风水物小说富少重金收了一块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
转载请注明:http://www.lojkk.com/ways/1193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