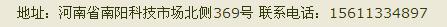中篇小说连载熊立功人性上篇
熊立功
上篇
“身子骨不舒服,你就莫上山了,我和你爹去就行。”
娘的话成了导火索。
“爹——他是我爹?狗屁!他根本不是!”
一时间,来顺胸口的坨子炸开了,粉碎着窒息的空间。
立时,娘那似冬日般的双眼背后凝固的冰块,在灼热的气浪中溶化,化作涓涓而流的凄凉,那冬日霎时间失去了光辉与充实,替代的是抽栗的灰暗。
爹在重重的喘息中,耷着头出了门,在他犁一般骨架后滚荡着一团紧裹的烟雾,在延伸的脚步中自拉成丝成线。
来顺为自己的鲁莽而惊骇,可他并不后悔。
本来,在吃早饭那刻,来顺胸口憋闷着的坨子在爹娘的殷情中就越来越大。
娘那冬日的光束在来顺周身温来暖去,可他总觉得那冬日的背后粘贴着凝固的冰块。那日头越是对他梳理,他越觉那冰块在紧固,娘没有吃,托着筷子娘专门给来顺添菜夹菜。
爹也没有吃,躬着米虾背,爹在吸旱烟,小口小口地吸,烟团在嘴里搅拌均匀后再慢慢往外吐,似乎总想将烟雾抽理成线。不时,爹把低垂的眼皮努力往上撑,拿淡黄的光束舔舔来顺。可每当迎上来顺的目光时,爹又象兔子般收回那热切的光点,在惊慌中变得零乱不堪。
爹是专门给来顺添饭的,到灶房要穿过院子。来顺不爱用海碗,一小碗一小碗吃了又添。往日,扒完最后一粒,爹就伸过老大的巴掌说我来,而那搁下来插在方桌缝里的烟棍吐出的青烟,与香柱没有两般。
来顺回来的这几天,爹和娘总这样侍候着他吃饭。可那刻,爹给他盛的饭,娘给他添的菜,来顺一口没动,他只觉得胸口憋闷得慌,那塞在胸口的坨子膨胀得快要爆炸了,他只想让那坨子裂开。终于,他如愿以偿了。
在爹娘马虎地吃完饭后,在他们清理着挖土取土的工具时,接上娘那关切的语言,来顺胸口那坨子炸开了。可炸开了,来顺又觉得胸口空洞洞的,一无所有。
不是省城的大爹,他来顺不会在清明节赶回黑土堡的。不是大爹,他兴许不会在二十五岁时,才滋生出那早该破碎的或不该生发的那胸口憋闷的那个坨子。
“五年小一祭,十年一大祭,这是我们黑土堡的乡俗。你该回去看看你爹啦。”
大爹虎着的脸划过一丝苍凉。他给来顺到学校请了假,他为来顺买了车票,还递给来顺一大包香柱草纸。
“你替我敬敬当地的先烈,为家魂野鬼烧柱香焚片纸吧,我,是不能回去的……”
神情茫然,大爹眼里润着愧色。
看身着笔挺挺军服的大爹,来顺心里不免有些惆怅。在这大扫迷信活动的岁月,作为军政要人的大爹,怎么还搞香呀纸的。后来,他才知道大爹为什么那么重视清明节,连那些野鬼也记在心里。
“我爹?什么人都不提,单提我爹,他不是活得好好的。”那时大爹把爹放在大祭后提出来,来顺很有些反感。
“对,你爹,都——都很好,总不会死的。”苦笑着,大爹结结巴巴。一向干脆利落的大爹,在来顺眼里变得来溜溜魂不附体了,原来大爹也有难堪的时候。
在来顺眼里,大爹永远是大爹,他是钢铁铸成的。他没有儿女情长,他永远与枪炮连在一起,他如军营般严峻。
八岁那年,来顺就被大爹带到了省城,更准确些是带到了只有绿、少许红的军营。论说他来顺该在黑土堡他娘手里读书的,可大爹怕他娘分心,带不好自己的孩子。来顺依稀地记得,那时,他们上路后,娘冬日背后那冰块被她的哭声溶化成骤雨的天空。他爹那坨背仿佛更加弯曲了,在他来顺的背后站成一座沉寂的大山。
对他,大爹没有促膝相谈的日子,有,也只是针对于他的学业。故乡黑土堡的历史,在来顺脑子里,大爹留给他的是一张空白,在他脑子里只有黑乎乎朦朦胧胧的群山,还有那古铜色肤肌的老实巴交的乡亲。
开始想,想爹想娘。他来顺思娘的体香思爹那总也闻不够的旱烟味,还有乡伯乡邻嫂们那疼爱的目光,一上床后他就带着这些碾转反复,许久之后才能进入梦乡,按着又用这些去填补去充实对故土的空白。
好我回,他吵着闹着要大爹送他回。大爹虎眼一瞪脸一沉,要他有出息时再回去,为黑土堡添添光增增辉。于是他便将自己对故土的思绪挂在笔尖,填进纸张的空白处,把对故乡的风土人情搁在墨字的深处珍藏。
如今,他来顺回了,回到了梦境里朦胧的故土,可很多事又让他憋闷的难受。自大爹送他上车那刻起,“你大了,该知道的应该知道,该原谅的不要耿耿于怀……”大爹发硬的余音,叫来顺的思维不得不象吸盘样,触向黑土堡。
胸口那坨子的隆起,不仅仅是大爹给他来顺的,还有黑土堡的乡邻。
“真是将门出将子啰,你出息啦,娃子。”
老实巴交的爹也能称将?该不是说娘吧,她是山里唯一通书达理的女人。
“噢,十几年不见,与你爹长的一样抽长俊俏,满肚文墨。”
抽长俊俏?爹可是弓腰驼背呀,满脸的沟回,象一兜遗露在外八方横溢的根须。记得几时爹教他诗句“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时,他就蹲在爹那扬溢的根须里,闻着爹身上的旱烟味;跟着爹喊了,还嚷着要爹教着写。摊摊手,爹说他没进过学堂门,样子很是苦涩,最后是娘过来解围的。
“我爹长得俊俏,还满肚文墨?”来顺皱皱眉头后向乡邻们摊出一个意想不到的东西。要命似的,乡邻们象周身爬满了毛虫似的,抓腮骚耳地慌慌躲闪,样子难受极了。又象一堆噼啪勃燃的大火遇上了一桶凉水,嗞地熄灭得只剩余温犹在的沉寂。
此刻,乡里乡邻们才感觉到来顺真正的长大了。在他们的眼里,来顺不再是十多年的毛小子了,而是一个堂堂的大学生,一个脑子能顶上他们所有脑子的现代人了。他们无意的吐露,使来顺自信的肯定,爹不是我的亲爹。于是,来顺那淤积在胸口憋闷多时的坨子便在第二天的早饭后破裂了。
娘没有再隐瞒来顺了,关于他们家血染的历史以及黑土堡的创伤。她清醒地知道,该儿子知道的事甚至不该让儿子知道的黑土堡历史的点滴,儿子如果想知道,他一定会知道的。
立在天河口,耸立在雾霭缭绕的坟岭,来顺犹如进入了仙境一般,恍恍惚惚的。他只觉得足下的土地在摇曳在抽泣,这是黑土堡祖祖辈辈安葬归天入地亡灵的龙虎之地。
二十二棵苍松合围成一个圆圈,撑掌出一个根色的天地,与那些灰黑色显露的岩石相应生辉,来顺亲爹就是其中的一株。
爹早已跪在亲爹那棵苍松的足下,与灰黑色岩石没有两般。没有眼泪,爹迟钝的目光刻进了眼前苍松的纹里,许久许久,爹磕撞起来,他的头磕得树杆咚咚作响,在松树抖动微曳中,爹似一头憋闷了一世的狂狮,疯吼起来:“二哥,我害了你,害了你是吗?你儿子来了,你给说说,给他说说呀!”
来顺惊呆了。
“跪下,给你爹磕个头,娘给你讲你爹,还有黑土堡的故事……”
娘的声息,仿佛自大山的深处爬出,又似来自于天际那空洞洞的世界。不,娘的声音分明是出自两片紧合的岩石间,伴着两股殷红的山泉。
三十年前的一个黑古隆冬之夜,嘶号鬼叫的山风,把紧裹在黑莽莽群山间的黑山堡,摆弄得喘不过气来。
黑山堡供奉祖人的祠堂内,松树的油结巴喷吐着噼叭作响的火舌,把个庭堂照得通亮火热的,铺垫着红幔的香案上,一字儿排开的十几个香炉里,燃烧的成把香柱,腾起紫色的烟柱,在庭堂内扩散成丝丝缕缕,将布衣山民们那些发亮晃动的光头置于古朴庄严之中。
“海小姐,你要教娃娃们读书做字,我们山巴佬可禁当不起啊!”
“海小姐,你的情我们领了,可……”
“你的老子我们可惹不起的。”
“真的哩,你是大富人的千金,跟我们这些山巴佬混在一起,你老爷会依么?”
火一样热烁烁的话,提心吊胆的忧虑,一齐喷向人围中婷婷玉立的海菊。
“大家不用担心,我定下的事,会走下去的!”海菊淡淡一笑,一双深沉的眼睛迎上一束束火辣辣的目光,“按族规行事吧”。
“好!”香案旁的一张圆手椅上站立着一身青布长衫的清瘦男子,他那张文静的脸在灯光下泛着红光。“族长不受理大家的事,我们就自个处理吧,我们总不能让黑土堡的后人永远目不识丁!”
“请来先生作主!”人围间滚出一阵热切的喧哗。
“兄弟,你就成个头吧,海小姐有盘活我们山巴佬后代的圣心,也不怕大富人他乱来!”呼声里站出了五大三粗的来斧头。
“好,我来秀才就听大家的了。”来先生向海菊投过去一腔敬佩,扫过黑土堡那些山巴佬迫切的期待,声音也就激动起来。
“……给海菊海先生行拜师礼!”
“你们敢!”象从阴曹钻出的一股寒风,使庭堂急剧地冷冻起来,山民们的冷汗一炸,就有根根汗毛倒竖起来。
一根乌亮的文明棍,在山民们的肉身上划出一条道来。大富人海胯子气势汹汹地立在香案前,对着青烟缭绕的香炉凝视片刻,然后一声狂吼,抡起文明棍扫荡起来,噼啪声过后,香案上的香炉打得粉碎,剩留着空中腾起的灰尖余烟。转过身,他一扫文明棍,对着面前目瞪口呆的山民,对他无可奈何的雇农佃户,低吼着说:“我女儿是谁骗来的?”
“我自个要来的。”海菊迎上那爹阴森的寒光,冷冷地说。
“不孝的东西,给我回去!”
“不,我不能老跟着你……”
“反了,你这辱门败户的东西!”海胯子手间的文明棍伴着吼叫声向海菊卷去。
横插进来,来斧头操起两只胳膊,一个紧合,把个大腹便便的海胯子连人带棍搂在怀内,嘴里低喝着,“老爷你可莫乱来,打伤的可是你的骨肉!”
抽开身,海胯子反手就是一棍,把来斧头打得火蓬。“你……”斧头的拳捏得咯吱发响。
“嘿嘿,你们活得不耐烦了是吧?别忘了你们种的田兴的地是谁的!神经作乐,一群不知轻重死活的疯子……”冷笑着,海胯子手间的文明棍扫过发愣的山民后,定在海菊身上。
“你回还是不回去?”
“不!”
“绑了,拖走!”
几个家丁在海胯子的嗷叫声里向海菊逼去。
“你总是讲个理吧。”来秀才一撩长衫,向海胯子面前大跨一步。
“叭!”秀才的头顶受了文明棍重重的一击。
“讲理?你这恩将仇报的小人,这就是理。”对着头昏目涨、眼冒金花的来秀才,海胯子挥了挥毒蛇般阴森浸骨的文明棍,在嘿嘿的冷笑声中,带着拖押着海菊的一帮家丁,走出了使人窒息的祠堂。
正了正身子,理了理粗重的呼吸,盯着扬长而去的海胯子,来秀才眼里喷出了源源不断的火。
作为黑土堡大富人的千金小姐,能从四季如春的绣楼上飘然而下,并很洒脱地走进黑土堡供奉祖人的大祠堂,要和他秀才一起,盘活木迂般黑土堡死了的活人。旁人是不解的,可他来秀才心里有数。
十年前,当他来秀才跟随着海胯子,步入为海菊一个人设立的书房时,他衣衫破乱的寒酸样子,遭到了天仙一般的海菊惊慌失措与鄙视。后来,在他的学业渐升为她之上时,她才知道黑土堡一个破落家子之所以能与她平起平坐,享用一个先生的资格的原由。
来秀才的爹,曾是这黑土堡的二富人,拥有仅次于大富人海胯子三分之二的田庄子。横草不拈,直草不端,光是收课收地租,也够他二富人享用几辈的。可坏就坏在二富人他不该染上了赌。本来嘛,要提赌,二富人的家诸器业全是靠他爹赌来的。因此,赌,在他二富人当家作主春风得意之时,他继续发扬光大,还赌,总赢。就连他三个孩子的名字都是他赌性正浓时给取的。
可后来,做梦也没想到二富人会栽在一向不嫖不赌的大富人海胯手里。只一夜功夫,家产、住宅、田庄子全输给了大富人,他们赌的是文房四宝。他二富人输得一塌糊涂,赌一样,输一局,结果再赌再输,最后连如花似玉的妻子也拱手相让了。
既然你二富人狠得心下,她贵夫人便也安得神。就在二富人魂归西天的那刻,来秀才的娘却披红戴绿,在吹吹打打的鼓乐声中,乘一顶花轿,离开败落的家,弃下三个幼儿,堂而皇之地走进了海胯子的偏房,做小去了。
当二富人脑子里冒出他的先生对他说的那句“读得书多胜斗丘”的真言时,已经迟了。先生对他说这句话时,是赤裸着身子哆嗦出来的。那时,他赌赢了先生的一身秀才礼服。
就在二富人喷出最后一坨紫色血块时,他总算还没有忘记一件顶顶重要的大事。从床上翻滚而下,跪头礼拜地,他乞求海胯子将他的三个孩儿中的一个盘出来,在学业上。
冲着跪在他胯下玉葱般娇嫩的秀才娘,大富人仁慈地点头了……
十年寒窗之后,来秀才做了黑土堡名符其实的秀才。海胯子也就完成了对二富人许下的诺言。很快,来秀才就被黑土堡的山巴佬请到大祠堂,供奉成与圣人般受人敬重的先生。
谁也没想到,第二年的第一天,十年前那个真实的故事,倒叫海菊随步而至,要与他来秀才一起,做酸秀才穷教书的,发誓盘活黑土堡活着的死人。
十天后,好说歹说而不改悔的海菊被她爹悬梁而吊。
“我要活埋了你,不忠不孝辱门败户的东西!……”
(待续)
顾问:(以姓氏笔画排列为序)
叶重豪江河
江长深张际春
金仕善徐绪敏
黄谷子詹学群
谭冰
主编:熊立功
编审:秦遥
刘银松
评论员:杨国庆
栏目编辑:
小说●李绍伦
散文●李天荣
诗歌●现代诗:
李其斌叶信于
倪先胜
古诗词:汪辉银
书画版:程常波
制作:李保全
投稿须知:
1,原创首发作品优先发表;
2,请作者提供个人简介、照片,经编辑审核推介;
3,谢绝抄袭、违法及侵害他人权益作品,文责自负;
4,20元以上,70%的赞赏作为作者稿酬;
5,驻《楚文学》选稿网络平台有搜狐网、今日头条、百度和《作家视野》;选稿报刊有《东坡文艺》《大悟山》《红安文艺》和《红色文化》报;
6,发表的作品,将择优在国家正规出版社结集出版。
7,郑重声明:《楚文学》所发各类文章,均系作者原创,各类媒体使用,须经作者本人授权同意,这里少数使用插图摘自网络,如有异议,请联系删。
8.收稿邮箱:
qq.转载请注明:http://www.lojkk.com/wazz/8863.html